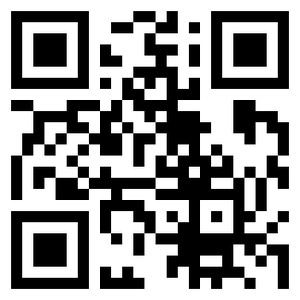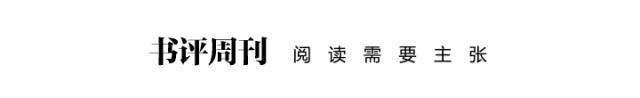
技术的发展让个人的健康管理得以成为可能,却也让人陷入“健康综合征”的焦虑之中:追求数据上的优异表现,忽视了身体和生活真正的需求。当我们从“自律使人自由”的标语中抽身回看焦虑背后的真实,会反复看到身体的有限性。“满分健康”并不存在国内正规配资公司,愈想支配就愈会带来恐惧。本专题的两篇文章,分别呈现了“满分健康”焦虑的剖析和在身体不那么完美的时候让自己好过一点的方法。它们共同试图回答:当健康被精确管理的愿望无法实现,我们该如何与不完美的身体共处。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8月8日专题《健康不需要“满分”》
B01「主题」健康不需要“满分”
B02-B03「主题」“满分”焦虑——从健身、节食到疑病症
B04-B05「主题」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修复指南
B06-B07「文学」多和田叶子 在幻想中书写冰冷的异化
B08「文学」唯有燃烧的爱,能将内心的隔膜融化
撰文 | 木三喵
我们总以为,只要够努力就能活得安全。运动打卡、轻断食、计算热量与体脂率,这些看似理性的健康管理,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对“健康满分”的执念。而当控制中断、数据反弹、自律失效时,涌上的不仅是内疚,还有深藏其下的失控恐惧。我曾陷入这样的循环,并在过程中逐渐意识到,问题或许不在于身体,而在于我们对“可控人生”的执迷。
健身、节食与体脂率:可操作化数据的诱惑
当一个人开始专注自身大多会干两件事,锻炼以及学英语。十年前就在网上听过这种话,现在依旧在有效期,又加了一项读书。学语言已不限于英语,多少人的生活是通勤路上在语言APP上打卡,打开电子书扫几行,下班后压缩睡觉时间来锻炼。这并不是什么美滋滋的事情。不久前看到有人从韩国网络“搬运”来的帖子说:“小时候看到30多岁的大人们突然开始运动时会想:哇他们这种悠闲自得真帅气啊。”接着话锋一转:“现在才知道,如果不运动的话,不久就会‘死’了。”
6年前我开始健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还没有到30岁,可当时体检数据已经有多项异常,体重更是飙到史无前例的新高。如果对健康水平按百分制打个分,大概有75分——没到良好凑合能活,不至于“死”到临头。那会儿我的态度是“随它吧”,因为焦虑只会新增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当回事。这是《精神焦虑症的自救》教会我的,它曾帮助我走过一段非常痛苦的焦虑期。但当时我不知道,如果一直不当回事,大脑就会强化这个想法和行为模式,让健康情况变得更不堪。改变源于室友看不下去我成天不动弹,去办健身卡时一定要拉上我。我们“I人”就是像孙书恒脱口秀说的那样,邀请一次拒绝,第二次继续拒绝,被邀请第三次,还不去是不是不太好啊……
《爱宠大机密2》剧照。
人一到了适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境中,多年被规训形成的想要“努把力”的意识就会泛上来,就差听到一句“能提分”。鸟鸟的段子说健身房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她一去就有人来卖课:“你有体态问题。”但接待我的教练看上去还没克服推销羞耻,全程都是我在主导提问:跟自己练有什么差别?多久能有效果?体检数据能变好吗?内脏脂肪能降多少?教练不敢就时间给出保证,甚至逃避直视我的眼睛,直到我抛出对自己而言的“必杀”问题:我能瘦回18岁吗?现在想起来,我忽悠自己的能力堪比赵本山卖拐。
一年以后我做到了,对不起自己的身体可以,不能对不起辛苦赚的钱。我一周固定上健身房3次,辅以极其严苛的饮食管理,虽然没有计算卡路里,但严格执行教练给的食谱,选择其中我能做出来的,并且尽量少吃。饥饿是可以忍受的,因为吊着我活下去的是体重秤上下滑的数字。当体重第一次卡平台期的时候,我开始极度焦虑,教练劝我说不要关注体重,要看体脂率。体脂率是人体脂肪占身体体重的比例,每个健身房和医院的营养科都有一台人体成分测试仪,原理是通过微弱的电流测试身体电阻力来推测各种成分的含量,还能计算出你不同部位的体脂和肌肉含量。刚开始锻炼的时候安排的都是燃脂训练,后期开始增肌,增肌就会增重,但是脂肪在减少。虽然体重没下降,你的身材会更好,身体也会更健康。同时,我也了解到16:8轻断食,在控制好全天饮食的前提下,将进食时间缩短在8小时以内,剩下的时间除了喝水、咖啡、电解质水以外什么都不要吃。这套饮食方法被明星广泛使用,并有文献证明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延长寿命。它还具备一定灵活性,你偶尔一天没按要求吃也没有太大关系。
来了,体脂率,一个量化的、科学的、有益健康的,还能偶尔偷懒的目标;饮食时间,一个直观的、有效的、简易的控制手段。这两者对于还脱离不了做题家底色的我极富魅力,进入社会以后很难再有像考试分数一样你知道该怎么努力还能确定地收获回报的东西。
自我量化管理:
从成功到失败
就像备考要有“头悬梁、锥刺股”的毅力,在追求低体脂的道路上我也在不断寻找对抗自己身体本能的“梁”和“锥”:实在忍不住想吃,就吃块纯黑巧克力压食欲;馋碳水馋得疯就奖励自己一口,但要蘸醋,因为醋可以延缓碳水吸收保持血糖平稳;如果馋重油重盐了,就是身体缺电解质了,补充电解质水,或者吃点香蕉。我下了一个减肥管理应用,每天记录自己的饮食,计算总卡路里。我严格执行16:8,每天10点到17点之间进食。如果前一天外食无法控制热量,第二天到晚上才会吃饭,这样两天摄入的总热量才符合要求,还可以消除没有控制热量的内疚。我还吃过一段时间的白芸豆酵素片,知名阻断碳水吸收的“智商税”。健身房依旧要去,工作再忙也没落下,隔一段时间还会来一节拉伸课,因为我有肌肉小腿,跑步十几分钟小腿会酸得不行。那不是简单的拉筋儿,是用手指或工具去推你小腿最紧绷的部分,一堂课下来我嗓子一定会哑,因为会疼得持续惨叫一小时。
严格的量化管理,让我在一年后一度达到19%的体脂率(我的起点是32%,成年健康女性一般在20%到25%之间),瘦10斤的效果看上去像20斤。内脏脂肪等级降到了4。一年后的体检数据也都变好了,除了无法消除的结节。我对生活的积极感知也在逐渐恢复,此时健康评分没到100分,但90分总有了,一种强大的能掌控自己的力量感萦绕着我。那段时间我是朋友圈里“健身改变生活”的信徒,我一时飘了,开始期待自己的体重能下100斤,让“定点体重”再低一点以给未来恢复正常饮食后留出更多空间。
《健康的迷思》
作者:(加)加博尔·马泰(加)丹尼尔·马泰
译者:姜帆
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5年4月
然而,这个目标没有完成。我的教练终于忍受不了健身房的剥削离职了。传统连锁健身房就像理发店,教练想要拿到课时费抽成就要拉够一定买课的预付费总额。倒霉的还会遇到“锁课推销”,如果不买新课,以前没上完的课就上不了。一想到再找教练就需要继续付费,新教练还不一定能快速了解我的情况,我决定以后靠自己不再续费。起初我还能坚持,随后问题接踵而至。我开始以工作太忙为理由不去健身房,反复暴食、节食、再暴食,我试图与自己的食欲和体重和解,不再称体重和计算卡路里。可没想到节食的尽头是复胖,不节食的尽头是更胖。
后来我也再找过健身教练,但再也没有当初坚持的劲头。高要求会影响行为的主动性,我就降低要求不再追求低体脂,可锻炼和饮食管理还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想起缺失营养素可能会引发食欲不稳定,就看了营养科医生,学习了膳食指南,查了身体所有营养素情况,但除了一直以来都有的缺铁无其他异常。健康分数肉眼可见地下降,内脏脂肪慢慢又长了回去。生活又回到了从前,我开始熬夜,不规律饮食,很久都不去体检。终于在一次测试人体成分的时候,我的数据全部回到起点。身体从“18岁”到30岁,这次速度快得我有点恍惚。
焦虑、内疚伴随不解,我对自己为什么不能回到从前充满了疑惑。多次我决定重新开始,恢复一切初始配置,却再也没有拿过得过的90分。我一度每天醒来无法对自己满意,快乐更无从谈起,唯有放弃挣扎和内耗,接受自己的失败。
拆解内疚感:健康综合征
“总是觉得自己运动量不够?在睡梦中计算卡路里?为自己没有感到更快乐而羞耻?那么,你可能已经成为健康综合征的受害者。”这段印在《健康综合征:当健康成为一种道德责任》封底的话,让我又开始思考起自己失败的健身经历。强行压抑不代表解决,只是一种节能式的抵御自责的方式。我依旧认为自己应该那样生活,只不过再也做不到。理论上我应该能从中强度运动中感受到内啡肽的快乐,内啡肽的分泌可以缓解身体在中高强度运动中产生的压力和痛苦,进而使人感到平静和愉悦。但此后哪怕我又一次完成40分钟以上的慢跑,也只有强迫自己完成的疲惫。
《健康综合征》是由两名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研究者撰写的书,它将“健康综合征”描述为一组持续的症状,你会因为自己生活得不足够健康而焦虑、自责、内疚。合著者之一安德烈·斯派塞在他们刚写完这本书不久做过一场同名分享,谈及他写作这本书是出于一个向内的思考——健身为什么没有让他获得快乐和意义感。起初他厌倦了无休止的漂泊生活、空洞的社交和无谓的享乐,想通过健身、吃有机蔬菜、正念、感知生活等向内的方式来摆脱不知道自己身于何处的恐惧。虽然我健身的出发点不涉及此,但后续状态良好的时候,将自己锚定在了一条我认为正确的道路上,一定程度缓解了存在焦虑。斯派塞对位置感的追求失败了,他的晨跑被另一名合著者戏称为“内疚跑步”——为了补偿前一天晚上的过度享乐。他按照健康的方式生活但内心却觉得进入了另一种生活的循环。每天早上醒来,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
《健康综合征》
作者:(瑞典)卡尔·塞德斯特伦 (新西兰)安德烈·斯派塞
译者:张璋
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6月
为破解这份自责,《健康综合征》援引了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阿伦卡·祖潘契奇所论述的“生物道德”,它指的是颓废和不满等坏情绪和状态正在越来越被视为道德上的过错和存在与生命本身的腐化,它提倡感觉良好而且快乐的人是好人,感觉糟糕的人是坏人。在这样的道德律令下,人如果不保持快乐和健康就会自责。健康开始成为一种命令。在命令之下,人们开始践行福柯所说的自我规训:自我记录、自我监控、自我管理。无法满足超我带来的要求衍生出更多的焦虑,数据的改善并不能带来与社会的链接感,也不能制止未来重归原点,这就会引发无意义感和内疚情绪。斯派塞就提到他报名参加马拉松比赛后忽视对家人的陪伴。内化了健康命令的我们用焦虑感惩罚自己,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中的这段是受困于健康命令的人们的写照:
“现在,放弃不再有彻底解放的效果,良性自制不再能换来爱的保证。岌岌可危的外在不幸——爱的缺失与外在权威的惩罚——被永久的内在不幸和内疚造成的紧张情绪取代。”
负面体验并非局限于个人。健康命令引发焦虑,就会有纾解手段的市场。内向思考、冥想、锻炼等自主文化产物被市场收编,它们可以协助人们适应周期性的经济变动,比如撑过裁员潮。这些背后都存在的共同点是认可个人是自主的、有力量的,能坚持不懈地提升自己,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这正是健康综合征的前提,它带来压倒性的责任感和选择焦虑,没有做到全是你的错,而无视了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所以《健康综合征》指向的批判对象之一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表面自由,让人们看似有选择的自由,并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代价。过去我们没得选,我们恨的对象有很多;现在选择很多且被标注了价格,我们只能恨自己选错、自己做不到或者买不起。
在公共层面上,健康与一个人拥有优良品质等价,一个爱吃垃圾食品的肥胖的人会遭到道德甚至能力上的鄙夷。健康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工作道德,如果你表现得不健康就无法胜任某些工作。反之,如果你在面试中说明自己擅长什么体育项目,会更有可能获得这份工作。“健康和幸福”已经成为公司和政府管理的指标,有公司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健身房和可提供健身功能的办公桌。免费的健身房、可以边工作边健身的办公桌、营养均衡的健康饮食全由公司提供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不好的,毕竟身边更多试图在工位上健身的人要思考的是买什么器材锻炼能保持低调,不被身边人理解为“工作量不饱和”。但当健康异化为生产力的工具,效率本身就会变成目的,无法胜任这套标准的人会被先天降一等。如果健康水平绑定着工资、升职空间和福利待遇,可想而知那并非人文关怀。
疑病症的土壤:“满分”焦虑与“失控”恐惧
回看我内疚的根源,也许正是曾经让我兴奋的起点。可操作化的数据一开始让我感受到掌控感,最后却转移了我对“健康”真正该关心的东西的关注——生活是否更舒适,身体是否自在,是否能从中感受到愉悦。体脂率比体重科学了一点,但它很容易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服美役”。一位有健身教练背景的写作者卢永利在《无限可能的身体》中反思了健康的概念说健康是生存的能力、体能是身体的表现。人们想让自己变得强健,但实际更期望的是好看的外表,而不是优秀的心肺功能和伸髋能力。
《无限可能的身体》
作者: [英] 卢永利
译者: 邬璐雪
版本: 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3年11月
在与食欲和解的挣扎中我看到了“生活化减脂”的提法:锻炼与饮食管理是一辈子的事情,不需要局限于短期的目标。起初这种长期主义观念让我稍感安慰:日子还很长,松一口气没关系。但这种温和的论调存在另一面:为了拿到“满分”你需要付出一辈子,而那种“做得不够”的羞耻将终身伴随。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运动机能与代谢水平将一日不如一日,想要维持“满分健康”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将一直处于这般的循环中——实在不行了,控制一下;一时没控制好,问题不大;反弹超出预期,又失败了。
除了健康命令之外,问题还在于我那被优绩主义塑形的健康观。在我的理解里,健康最好是一个静态标准,它应该是可抵达、可维持、可在达成后按下暂停键的。而从小接受的教育体系也让我习惯了“考试结束就能放假”的状态,终极考试结束后可以获得彻底的解放。我的身体似乎天真地以为,哪怕理智知道那并不对,只要拼一把,就可以迎来稳定的“合格人生”了。我巅峰迎战高体脂的状态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提前透支。在坚持轻断食的时候为了抚慰深夜里空洞的胃,我会捏自己的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感受皮下越来越薄的脂肪层直至入睡。事实上,我并不喜欢运动,也不喜欢抗阻力训练,计算食物热量在降低我进食的快乐。承认这一点有一丝羞耻,毕竟我付出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但真实情况就是在一次透支带来的失败之后,身体很难再鼓起劲头。
我控制了外在变量但忽视了自己,身体不是考试,它是流动的、变化的、带着衰老节奏和脆弱底色的。出问题的是我对静态的满分健康的幻想。而这种流动的健康,也让我想起了以前经历过的疑病症的焦虑。当时心脏不舒服,低烧持续一个月、住院三天又没有查出任何病因,医生说症状像某种需要终身服药的疾病但检查结果不完全支持,可能也没什么问题让我回家观察看看。我不再上网查症状,不再讨论身体,但恐惧和焦虑让我在半年时间内看了三十多位医生却毫无结果,他们告诉我这个科室相关的病我没有,回家吧。诡谲的是我爸年轻时的时候也有一段跟我一模一样的疑病期。我们后来都选择了看中医调养,慢慢不把它当回事,身体就渐渐康复了。
图/IC photo
再一次,压抑和躲避暂时解决了问题,却没有改变我根深蒂固的思维。这段往事浮现于眼前,正因为我感受到它与我对“满分健康”的执念有同样的逻辑:只要努力一把,我就能回到期待的状态,或者把状态控制在我能接受的可控的范围内——追求“满分健康”,是为了未来有降分的空间;体脂率、锻炼时间、体检报告数据甚至是医疗保险,它们像是数字版的护身符,延宕我们应对未知危险的恐慌。我们当下的健康焦虑,包括疑病症、饮食焦虑、健身焦虑等有一个共同的土壤——我们惧怕“失控”,我们也在惧怕我们的努力没有用。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恐惧》中写道:
“‘衍生恐惧’……是一种对于危险的怀疑情绪,同时也是一种不安全感和脆弱感……而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脆弱感,不是因为实际威胁的能量巨大或者极其恶劣,而是因为人们对于所能采取的抵抗措施并不信任。”
面对恐惧人们本能地想要逃避,但蔓延的不确定性总会在某一时刻提醒你它的存在。此前我因为轻微的髋关节撞击导致左髋疼痛和骨髓发炎,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结果问你做了什么剧烈运动——我只是坐了一趟高铁,在B座。
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读到了《健康的迷思》,这本书反思了身心健康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确定性的压力、冲突和缺乏掌控感等都会导致压力应激,而慢性压力会因为加剧身体的炎症反应导致更容易患上疾病。所以一个把别人需求置于自己需求之上的好人,一个擅长自我反思、自我攻击导致与自我感受剥离的人,会因为背负过多的个人责任感而增加健康风险。揭露真实会带来恐惧,“晚期资本主义很擅长应对”:“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之间的隔阂变得越来越大,并且用虚假的产品与人为的、分散注意力的消费文化填补这种隔阂。……归根结底,我们忽视的就是生活本身。”
改变需要长久和艰难的工作,关乎医疗、法律、焦虑等方方面面。庞大的问题让人难以预料未来会怎么样,作者在研究中曾与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家诺姆·乔姆斯基交流,问他是否对未来感到乐观。乔姆斯基笑了,他引用了葛兰西的一句著名的口号:“理性上的悲观主义者,意志上的乐观主义。”然后说道:
“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木三喵;编辑:宫照华 走走;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国内正规配资公司
倍悦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